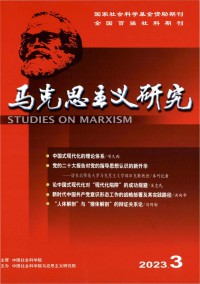马克思颠覆形而上学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颠覆形而上学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就是运用思维的“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而认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这种反本质的观点,又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哲学语境。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并不存在“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旨在剥离它的唯心论外壳,决非要去颠覆它。
关键词:形而上学;马克思;黑格尔;颠覆;后现代;哲学
一
马克思认为,统一的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棗精神的掌握的。”[1](104页)在这里,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理论(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以及宗教、“实践椌瘛彼嘉绞降牟煌刂省*?/P>
那么,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0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确切地说是深藏在现象之中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停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
这种不发达的“抽象力”使李嘉图只能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而不能发现剩余价值本身,即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
马克思说,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任何理性、观念只能是现象背后(或现象中)的本质,而哲学和科学理论也只能运用人类的理性能力从感性的杂多现象中抽出本质,从而摆脱杂多的感性现象,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予以研究和规定,“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1](107页)。而且“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2](283页)。这样看来,《哲学研究》2002年第4期仰海峰先生在论文《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中所谓“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颠覆,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并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加以规定,这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3]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在学理上这种反本质的观点,又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哲学语境。正如江民安先生所说:“后现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巨型幻觉来祛除的。”[4](003页)
为了证明所谓的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仰先生引证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派运动的评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3]。但是,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阐明的中心主题是说明哲学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5](23页)。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出所谓“颠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个与哲学同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两类不同的哲学问题。
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6](145页)。但是,从宏观上说,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共同的,只是在微观的解答方式、形成的具体思想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同现实联系的一种错误理论,不能把它曲解为任何哲学可以离开理性思维,从而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着的事物的本质称作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就一方面会导致对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否定,另一方面又必然陷入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之类的哲学的末途。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的代表萨特等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现象的本质,存在已经失去了本质,所以现象本身就是存在。而这种存在的现象是不能靠思维的力量揭示出来,只有靠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焦虑等非理性体验才能显示出来。如果说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在现代哲学发展史上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使这种现象学完全蜕化为表面哲学。江民安先生说:“我们回到了表面哲学,这正是后现代性抛弃本质和真理的必然归途。”[4](005页)
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在黑格尔以前,“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只有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才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静止的、孤立的、不运动、不发展的思维方法;一种仍然是属于哲学本体论的,也就是哲学自身。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厚重性是任何新哲学所难以颠覆的,或者说在根本上是不可能颠覆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所显现的是“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7](191页)。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青年马克思是如此,老年马克思也是如此。以致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17?/FONT>218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而仰先生却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混淆,即将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3]。但是,我以为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那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所指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论断都是不可分离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410页),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学说。以致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令人无穷回味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191页)很难说仰先生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评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把认识过程与表达过程分离开来,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它乃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大景观。仰先生与此相似,引证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原则,这种任意性不仅体现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也是任意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基础。”[3]的确,哲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努力寻求它的语言学表述,因为哲学靠思维的“抽象力”从感性杂多的现象中抽出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ν),又是展示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εγομενον),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9](23?/FONT>24页)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也是错误的。而且索绪尔本人的观点也前后不一致,他一会儿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会儿又说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的,因为:“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10](107页)。因为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0](107页)我以为既然语言对使用它的社会来说是强制性的,因而对它表示的观念来说也有强制性,因为观念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5](525页)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地位受到了动摇”[3],那么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
仰先生还说:“哲学的表达过程并不能否定理性的产生过程,这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忽视,反而成为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前提。”[3]我怎么也弄不懂黑格尔在哪里用“哲学的表达过程”否定了“理性的产生过程”?!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处处看到他把“理性的产生”与“哲学的表达”紧密地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但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这首先表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了精神即理性诞生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致最后达到了“绝对知识”,达到了哲学。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Dialektik)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辩证进展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观点的必然性”[7](93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11](215页)。《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形成史。在这里,理性的形成,黑格尔是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的,这种语言是既晦涩,但又包涵着丰富辩证法和逻辑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针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也说:“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棗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棗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12](165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产生和它的哲学表达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致,不存在仰先生所谓的矛盾和忽视。后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还说过:“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13](9页)。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理性具有明显的能动性,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这种能动性必然能够寻求到与自身相符合的语言学表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哲学与语言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使哲学家的思考在语言载体的基础上更有成效。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思想之实事并不是通过发动一场关于‘存在之真理’和‘存在历史’的空谈就可以达到的。一切都只取决于:存在之真理达乎语言而思想进入这种语言中”[14](405页)。
二
仰先生在虚幻地设置了黑格尔将“理性的产生过程”和“哲学的表达过程”的分离性后,又说“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3]。首先我要说把成熟时代的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机械地分割开来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它只是仰先生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假想。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D·沃克尔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方法的要素与演进》一文中已经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就连他思想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变化,也伴随着与他早期思想的各种承续”,“即使承认《费尔巴哈提纲》代表的重大革新,也没有必要把这篇作品看成是与马克思以前思想的一种彻底决裂”[15]。马克思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支持仰先生观点唯一重大的理论根据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任何想寻求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式的理性,都成为一种幻想”[3]。事实决非如此。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不断流动、生成、变灭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运动的过程。因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不仅是有与无的统一,而且是内在的不安息”[7](198页)。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但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显然,马克思与仰先生的论断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在思维中已经颠倒地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表示出来,这就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马克思说:“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12](172页)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在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中,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马克思在早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研究时已经深刻地把握了这种流动性。但黑格尔却是用他的形而上学理念概括了这种流动性,并把它们结构成了运动的环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中也说过:“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8](267页)。所以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并不是远离了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思辨地具体地把握着了他生活的时代。仰先生继续写道:“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只要他们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纯粹理性革命就会出现其神话的本质。”[3]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仰先生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诚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首要原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同时认为,意识对生活具有反作用。然而,理论对现实的反作用在仰先生的论述中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年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指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6](592页)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以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新哲学去面对现实,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实现对现实的革命变革。所以在这里与仰先生的论断有所不同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提出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纯粹理性革命可在一方面出现它的神话本质,例如在鲍威尔等人哪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运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曾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
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6](591页)这就是说,当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青年黑格尔派必然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例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继续兜售黑格尔绝对精神解体后被分化出来的Caputmortuum;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黑格尔哲学所指出的通往现实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又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棗尤其是棗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16](591页)
我以为仰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通常的哲学错误,即片面地执著于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对形而上学的决定作用,但忽略了形而上学是人类头脑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最高抽象,是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超验思考,是一种远离社会生活的思维活动,是“高耸入云”(恩格斯语)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就是以“回归现实生活”来反对哲学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但是离开了哲学本体论,人类必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在超越的本体界,人的思维才能不受他物的影响,一切“出自”“自己”(叶秀山先生语),把哲学提高到自由的境界,从而发挥哲学超强度的信念力量,塑造高尚的理想人格。由于对“抽象原则”的轻视和拒斥,使西方一些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沦为一种浅薄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美国存在主义者巴雷特就曾经指出,现代西方人已变成了三重异化的人:与自然、与其他的人、与自己异化的人。正由于如仰先生所说“福柯将现代意义上的疯癫看作是近性进行区隔的结果”[3](其实福柯并未停留在将疯癫看作是对近性的区隔,他以他的全部非理性主义极力证明疯癫是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中活动),因此福柯哲学的边缘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江民安先生在《后现代性的谱系》中在评述福柯的考古学时所说:“考古学不是别的,它正是要使那种历史中的沉默体、边缘体、异质物重现、出声,要让它们呼喊或细语,要让一切怪异物合法化。”[4](009页)这里所谓一切“怪异物”是什么东西,读者可以读一读福柯的著作就会清楚了。其实,“疯癫”被引入哲学并不是福柯的发明,早在叔本华那里,对“疯癫”就作了入木三分的阐明(在文艺复兴时代,疯癫大致只局限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爱拉斯谟的《疯狂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不过,叔本华对疯颠是否定的。他说:“疯癫如果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产生完全失去记忆的现象;因此这个疯人就再不能对任何不在眼前的或过去的事物加以考虑了,他完全只是被决定于当前一时的高兴,联系着他在自己头脑中用以填充过去的幻想。所以接近这样一个疯子,如果人们不经常使他看到[对方的]优势,那就没有一秒钟能够保证不受到他的袭击或杀害。棗疯人的认识和动物的认识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是说两者都是局限于眼前的;而使两者有区别的是:动物对于过去所以是根本无所知,过去虽以习惯为媒介而在动物身上发生作用,例如狗能在多年之后还认识从前的旧主人,那就叫做从主人的面貌重获那习惯了的印象;但是对于自从主人别后的岁月,它却没有什么回忆。疯人则相反,在他的理性中总还带有抽象中的过去,不过,这是一种虚假的过去,只对他而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是经常的,也可以仅仅只是当前一时的。虚假的过去的这种影响又妨碍他使用正确地认识了的‘现在’,而这反而是动物能够使用的。”[6](269页)因此,我以为要像福柯那样对理性进行绝对的区隔,哲学就不再是人类的哲学,而质变为兽性的体验,那么,换妻俱乐部、裸体游泳场、野人屋……将不断出现,人类也将倒退到洪荒的动物时代。而且按照叔本华的理解,这种倒退到的程度,还低于动物的水平。马克思也有类似论断,说人一旦失去理性,他就比最凶猛的动物更残忍、更可怕。
三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与动物具有本质区别的“人之生存如何可能”,在我们面前立即展示出三种哲学维度:第一,“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社会维度;第二,“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理智基础上的伦理学维度;第三,“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形而上”维度。如果说第一种和第二种维度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础维度和高级维度,那么,“人之生存可能”的“形而上”维度则是它的终极维度。这种维度不仅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是人对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追求,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生完善的追求,是一种绝对的追求,它始终指引着、甚至规范着人的当前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和具有历史暂时性和相对性的政治伦理现实。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感性,甚至理智(即悟性)中去实现,只能在理性中展示她的真、善、美的价值,因此它必然是剥离了具体时空的、超越人的当前存在的纯真的精神境界。当代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也说:“从根本上说,因为人身上总有某些东西无法被世界社会满足:对真实、高贵、伟大的渴望。这些渴望表达在人的理想中。”[17](129?/FONT>130页)古希腊哲学家的贡献就是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研究现象世界,而是要探讨现象背后的根源和本质,因此哲学的最高本体必然是“被剥夺了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始基”,这一伟大贡献使上千年的哲学史得以延续。但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点又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他说:“这就是抽象的‘一’与‘多’的关联。这种关联恰恰是唯心论的。”[3]仰先生还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第一次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去中心化过程”[3],这又是仰先生的虚构。(当然,福柯等人把马克思和尼采、弗洛伊德拉扯在一起,说成是“去中心”的开创者,也是一种天国的神话。)实现形而上学去中心过程是起始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而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达到了它的颠峰状态。而马克思的一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哲学中心论的。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就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棗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16](121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已成为“哲学的世界”,正是马克思十分肯定地确立了哲学在人类思维中的中心地位。而且,马克思还对他的论敌尖锐地指出:“但是,哲学谈论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经过研究就谈论这些问题,而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感觉,哲学则求助于理性。”[16](123页)“‘自由理性的行为’我们就称为哲学研究。”[16](125页)如果我们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实事求是地研究西方哲学史的话,那么应当承认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或者说是它的核心,它的本质是一种沉思的生活。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证哈贝马斯的话说:“‘哲学则把过沉思的生活,即理论生活方式当作拯救途径。’因此,意识革命只是一种古代神话的当代再现,这是一种想象的革命、一种跪着的造反。”[3]这种说法又与马克思的论断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棗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作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16](120页)但是,“哲学就其特性来说,从来没有打算过把禁欲主义的神甫法衣换成报纸的轻便时装。然而,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16](120页)。因此,“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16]〖HT5”SS〗(120页)〖HT5SS〗。从马克思的这些话中,我们看到“沉思”并不是什么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家在“沉思”中构筑哲学体系就如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一样地实在,因此哲学的“沉思”的革命性远远超过了那些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回归”的爆炸力。“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15](121页)。所以,在这里被仰先生引用的哈贝马斯的反讽恰恰是歪打正着,哲学正是通过理论的“沉思”而拯救世界,“沉思”是每一个真正哲学家的宿命。当然,这种“沉思”又必须是对生活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的、甚至是有关人类命运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在40年的“沉思”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打击,远远超过了“巴黎公社”那些英雄们带有盲动性的“壮举”,是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构和颠覆。康德的“沉思”给封建主义制度的沉重打击,胜过了实实在在的千军万马,卢梭的“沉思”使罗伯斯庇尔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与仰先生描述的绝然相反的景观,因为在仰先生那里只把哲学作为一种静观的思维,而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回避思维产物对历史的巨大的反作用。诚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一旦放到现实生活中,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然而,仰先生却说:“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形而上学的颠覆并不能靠将之放到社会历史生活中就可以解决,而是要通过对社会生活本身的颠覆,才能实现对旧形而上学的真正颠覆。”[3]这又是与马克思的精神相背离的,而且也是与仰先生自己所说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在于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精神,走向对当下生活的批判性解构”相背离的。如果我们不在哲学术语上过分的纠缠,那么我以为只有将形而上学即哲学“放到社会历史生活”中,才能实现“对当下生活批判性解构”,而且也才能解构一切错误的哲学理论,因为理论的矛盾和对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超验的理性、观念,绝不如仰先生所说的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超验世界同样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的真实性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用思维着的“头脑”去把握。而“形而上学”即哲学之所以能如康德那样百折不挠地寻求纯粹先天先验的根据,也即是寻求纯粹逻辑在先的根据,因为这正是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终极思考。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以“求知”而谈哲理,并不是远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一种完全彻底入世的思考,它厘清了语言与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修辞学、逻辑学、认识论、美学、伦理学等分支部门。柏拉图的《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既是他们抽象哲学理念的具体演绎,也是他们入世的宏伟宣言。而从整体上说,这也就是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中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困惑着柏拉图、也困惑着亚里士多德,它通过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直达康德,最后在黑格尔那里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完成了它们的统一。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它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8]〖HT5”SS〗(410页)〖HT5SS〗我以为仰先生也没有注意到。因为理性揭示的一般本质决不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遐想”,而是通过感性的个别而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的,正如列宁所说,“个别就是一般”。黑格尔又把它解释为“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认为“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离开了“有限”的“无限”是“恶无限”。因此黑格尔在这里也就从方法论上决定了不能如仰先生那样把形而上学机械地分割为以绝对为根基的和只肯定有限性的两种形而上学。至于说到“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差不多有一种共识,那就是“拒斥”的开始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发起的猛烈攻击,源于它认为知识的陈述只能与经验相关,而知识的证实也只能在经验中获得。这种只承认经验的事实,只承认现象存在的哲学源头可以回追到休谟那里,因为休谟据此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发动了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但是休谟的攻击并没有达到目的,最后还是回归到了形而上学。休谟的思想启发了康德,使康德继休谟之后对形而上学发动了又一次攻击,但结果是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又建构了一座巍峨的形而上学大厦即“批判哲学”,而且明确地指出,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没有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尼采对古典形而上学的攻击更是猛烈强劲,以致尼采用“虚无主义”来概括一切古典形而上学,认定由于古典形而上学的产生和存在造成了西方哲学虚无主义的历史。但是,哲学发展的进程大大地嘲弄了尼采。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尼采对古典形而上学的反叛,“不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而是“对虚无主义的最终介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并没有斩断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反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实实在在的尼采虽然疯狂反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但却在另一方面维护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一种生命本能的形而上学。尽管有人可能说我在十年前发表的文章《理性的陨落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篇单纯谩骂式的哲学吊诡,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引用我在那篇文章里说过的一句话:“在酒神精神的发源地棗《悲剧的诞生》中,狄俄尼索斯精神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沉思,是尼采对人生、世界、宇宙的根本哲学解答,这种解答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酒神精神使我们在悲剧艺术和悲惨事件背后,感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狄奥尼索斯的激情转化为哲学激情’”[18]。尽管有人认为是尼采首先解构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甚至认为“尼采不仅仅使形而上学转向,他还根本性地使之扭断”[4](002页)。但是,我以为尼采的全部哲学仍然是运行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路轨之上的。海德格尔似乎比尼采对形而上学更加不满,他以“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为由,认为历史上的一切形而上学都遗忘了存在,又一次发动了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但是海德格尔的命运并不比尼采好了多少。海德格尔步尼采哲学之后尘,企图把“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结合起来,认为历史只是“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和“自由流变”。试图以此来“完成”尼采的遗愿,终结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但由于海德格尔面对的是处于西方传统哲学问题中的尼采,这就使海德格尔不能站在形而上学之外,而必须站在形而上学之中。正如德里达所说:“要颠覆形而上学,没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语言棗句法和词典棗都不是外在于历史的,显然,我们所提出的任何一个破坏性命题无一不是已经包含在它试图予以抗争的那种形式、逻辑和内在基本原则之中的。”[19](前言9页)所以海德格尔在对形而上学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猛攻之后,终于败下阵来,不得不得出一个他自己极不愿意看到的结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且像康德一样在破坏了的旧基地上又建立了一座海氏的形而上学大厦。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说:“甚至任何一种对‘存在’的追问,也包括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首先亦必须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地’追问来进行。”[14](377页)
四
海德格尔被某些哲学家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始祖,后现代主义哲学继海德格尔之后又掀起了更加强大的解构一切形而上学的狂潮,这就是所谓“后哲学文化”。但是人们如果不遗忘历史,认真研究后现代主义哲学,人们可以看到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都在重新构建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一切真理一样,但“没有真理”就是他们的真理。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在“人之生存之所以可能”中,“形而上”的沉思是最高的维度,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形而上的沉思可以表现在逻辑中,也可以表现在非逻辑中,但归根到底它是不能脱离人的“理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面对黑格尔所构建的理性形而上学体系,虽然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地方尖锐地批评过它,但我们仔细研究也不难发现,马克思也曾经大力赞扬过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20](159页)。对于黑格尔所建构的哲学体系,我以为马克思并没有去颠覆它,而且马克思也没有想过要去颠覆它。因为正如利奥·施特劳斯所说,“黑格尔是第一位认识到其哲学从属于其时代的哲人”[17](126页)。哲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然黑格尔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也会被时代所扬弃(决不是颠覆)。但是,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棗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21](2页)我国著名学者王树人先生是这样诠释黑格尔这句话的:黑格尔其所以这样评价形而上学,是因为他把形而上学看成民族魂和民族精神的本质。所以,我以为,晚年的马克思称自己为黑格尔的学生是不可能颠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的,而且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就已经为后人指出一条走出体系迷宫的道路,虽然黑格尔本人十分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必然的历史使命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本文就不必在此多说了。至于马克思是否“在理论的深层上,也颠覆了海德格尔式的形而上学”,我想恐怕仰先生在此说得太远了,论点所及已远远超过了他文章的主题,而且这种逻辑推论实在令人费解。因为在海德格尔之后,甚至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之后,又有一些哲学家在重构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那么马克思是否又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颠覆了这些“形而上学”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仰海峰.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J].哲学研究,2002,(4).
[4]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A].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邓晓芒.思辨的张力[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14]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A].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5]沃克尔.马克思晚期著作中方法的要素与演进[J].世界哲学,2002,(2).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ZK(〗利奥·施特劳斯.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A].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集):第六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ZK)〗
[18]姚定一.理性的殒落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19]德里达.写作与差异.转引自: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0]马克思恩格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