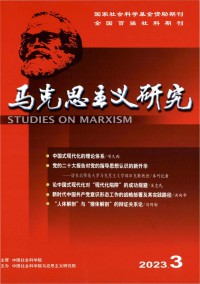马克思信仰思想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信仰思想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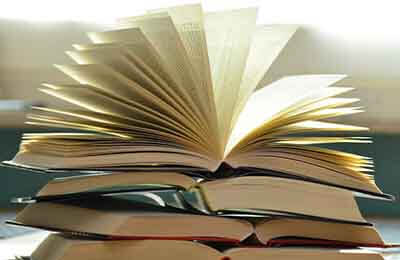
内容提要】马克思从经济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信仰问题,揭示了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经济基础。他从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方面来考察神话的起源和本质,认为神话是人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从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上考察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揭示了宗教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分析了基督教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认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形式;分析了信仰自由原则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分析了市场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之间的联系;分析了作为经济现象的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信仰意义,认为它体现着人们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信仰/宗教
【正文】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一、从经济看信仰: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经典作家从来不谈论和研究信仰问题。这种印象不正确。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就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马克思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谈论过信仰;从批判旧哲学和清算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政治斗争和政治信念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人生信仰角度谈到过信仰;还从思想宣传的角度,以及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等也谈到过信仰问题。在马克思谈论信仰的各种角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至今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视角,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仰现象的观察和透视。这是马克思信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信仰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现象,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历来研究信仰现象的人,不论是一些神学家、宗教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等,往往从思想人文的角度考察信仰问题,而通常并不注意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独具慧眼,能够从经济角度去考察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理论分工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因而,他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随时随地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颖的见解。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作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等就是如此。另外,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象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①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②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二、关于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几个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1.神话: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宗教信仰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宗教信仰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学习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③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历史阶段,人们更多地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是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其实,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有差异,但并不完全不同。宗教世界观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对神话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神话的出现比系统的宗教世界观要早,因而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力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而随着从不自觉的神话创作到系统的宗教世界观形成,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来越被神学掩盖了,在宗教教义中,人们只能看到神的意志和要求,看到人对于神的皈依和崇拜,而看不到人类自身力图改造世界的要求了。因而,通过了解神话的本质作用和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揭开宗教信仰的秘密。比如,从神话中看到,宗教不过是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分化产生出来的,这就看到了宗教的世俗起源,扫去了它的神圣光环。随着自然力(以及社会力)在实际上被人类所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宗教也会随之消亡。
2.宗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对他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种现实的关系是合理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明朗的而不是神秘的,那么这种世界观上的反映就是真实的反映,而如果这些现实的关系是狭隘的而不是合理的,神秘的而不是明朗的,那么对这些关系的反映就往往是幻想的,即宗教的。马克思写道:在古代,“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马克思认为,宗教正是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古代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狭隘性,现实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神秘性。随着这种神秘性的消失,宗教的反映才有可能消失。
3.基督教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⑥恩格斯加以概括说:“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⑦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基督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一神教的神是万能的,“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⑧。基督教对耶稣这样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的崇拜更突出地体现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抽象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从封建束缚中独立出来,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联系,而是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隔离。个人劳动只有作为抽象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个人只有作为抽象的人才是社会的人。所以,就像抽象的人的代表(耶稣)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的代表(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是由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原则之间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就像基督教中人们对基督的崇拜一样,是一种对中介者或中介物的崇拜。马克思写道:“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⑨“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⑩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接近上帝,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上帝也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崇拜,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且,由于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因而也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由于都相信基督而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彼此联系起来。同样,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个万能中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在个人劳动面前代表社会劳动,在个人面前代表社会,同时在社会面前代表个人,在社会劳动面前代表个人劳动。这样一种万能中介物,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崇拜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万能媒介,它的作用使它引起了人们的崇拜,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马克思指出:“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11]
马克思在讲到基督教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宗教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认为它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更为适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正是西方一些学者目前研究的所谓“韦伯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欧并在那里最先得到完备的发展,是由于西欧在宗教改革中首先形成了一种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引发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很多人赞成。其实,首先提出和研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与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好相反:韦伯是用基督教新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而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明新教的产生。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更为清晰,也更为正确。基督教新教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宗教,当然是更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式。
4.信仰自由是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在这里,“自由竞争”不是别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思想信仰领域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经济领域及其变动。统治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原则反映到社会的思想领域中,反映到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形成了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通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说明,是马克思的视角创新和观点创新。在此之前,人们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往往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讨论的,是从思想的宽容、宗教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等等角度谈论问题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原则。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考察社会的信仰现象和对待信仰问题的原则,得出了最深刻科学的解释。
三、商品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察商品经济与信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以下几个问题中的考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导。
1.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顾名思义,它们分别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三者是一致的,逐步递进的。
马克思最先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概念,马克思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人们对于商品的态度称作拜物教的。马克思用宗教中的拜物教概念来比拟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和人们对这种假象的迷惑和崇拜。他写道:“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2]意思是说,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独立存在的物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它与宗教中的拜物教相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
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性质相同,不过在形式上更集中、更突出和更耀眼。“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4]正因为如此,“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15]
货币拜物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粗糙的形式即贵金属崇拜,它是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另一种是精致的形式即对钱的崇拜,它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现代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16]“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17]
资本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在资本的各种形式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18]“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9]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拜金主义的问题有深刻启示。首先,金钱崇拜是以商品崇拜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就可能产生对这些特点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对商品以及货币的崇拜,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更为突出了,金钱崇拜也更为耀眼。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思想意识领域积极地反对拜金主义,把这种错误倾向削弱到最低限度。其次,金钱崇拜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崇拜。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迫切希望金钱的自身繁殖,而资本崇拜则正是表现出货币自身繁殖的外观。如果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直接地表现出政治倾向,并不直接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则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金钱拜物教向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的演化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2.信用制度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
马克思对信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揭示了信用和信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了在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念中,在对一国货币的信任中,体现着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这信念可以说是人们社会信仰的一部分。
信用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0]在马克思看来,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信用业,也就是说从货币主义到信用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进步,支撑这个转变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们对商品内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着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马克思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进步,也不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天然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与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1]
【参考文献】
①②⑤⑥[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98页、105页、96-97页、96页、89页、88-89页、111页、1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66-667页、6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77页。
⑨⑩[11][16][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9页、19页、19页、20页、21页、21-22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440页、442页。
[20]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