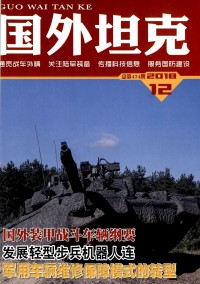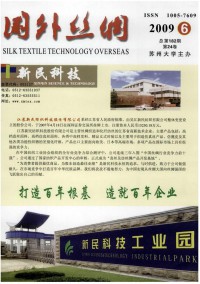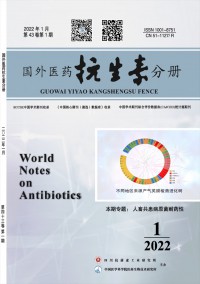国外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国外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苏联文学理论自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以后,成为革命文学的主导思想;以后,苏联文学理论又中国化了,形成了文艺思想。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这导致二者之间由合作到对抗,直至发生“反修”、“”。这一段历史经验尚没有加以总结,有必要进行严肃的学术考察。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首先,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苏联文学理论循着欧洲认识论传统建构体系,建立了反映论的文学观,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而文艺思想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论传统,弱化文学的认识功能,强化文学的载道功能,是一元化的文学思想体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出发来论述文学的本质,而是从社会功利目的即“文学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命题出发展开论述。这预设了一种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本质观,即文学代表着主观价值,与客观认识和反映无涉;这与苏联文学理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后来愈演愈烈,导致了二者的分道扬镳。虽然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但是,他仅仅在谈到文学创作的源泉时才使用了反映概念,而且从全文看,也仅是个别论述,并没有成为基本的观念。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社会功利作用,而不是文学的客观性、认识作用。他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他还说:“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这种功利主义的出发点以及意识形态论前提,与“文以载道”的传统论调不谋而合。这篇讲话,在逻辑起点上,向传统文论回归。
同时,对文学本质问题采取了实用理性的态度,而不是科学主义态度。他在讲话《结论》部分的开篇处着力批驳了从本本出发的文学观,主张从实际出发,文学为现实服务。“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3]这种阐释策略,回避了苏联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论界定,暗中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他找到了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和马克思实践论的平衡点,增强文艺思想的合法性依据。而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便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以及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纪梦想。
其次,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修正,突出强调文学的革命理想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六个更”实际上突出了文学的理想性,用革命理想主义的神圣光环来矫饰和美化现实,以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情怀,从而推动革命进程,使文学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思想避免了苏联文学理论二元体系的内在矛盾,让文学真实性服务于意识形态性。明确提出“以写光明为主”的创作指导思想。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改造,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乐感文化”精神、大团圆模式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大众化”文艺思想,并且主张民间化的文学路线。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反资本主义、大众化、集权化、道德化以及大众崇拜等特征。厌弃西化路线,终其一生苦苦追寻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他带有浓厚的大众意识,不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依靠农民,走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首先,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苏联文学理论循着欧洲认识论传统建构体系,建立了反映论的文学观,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而文艺思想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论传统,弱化文学的认识功能,强化文学的载道功能,是一元化的文学思想体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出发来论述文学的本质,而是从社会功利目的即“文学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命题出发展开论述。这预设了一种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本质观,即文学代表着主观价值,与客观认识和反映无涉;这与苏联文学理论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后来愈演愈烈,导致了二者的分道扬镳。虽然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但是,他仅仅在谈到文学创作的源泉时才使用了反映概念,而且从全文看,也仅是个别论述,并没有成为基本的观念。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社会功利作用,而不是文学的客观性、认识作用。他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他还说:“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这种功利主义的出发点以及意识形态论前提,与“文以载道”的传统论调不谋而合。这篇讲话,在逻辑起点上,向传统文论回归。
同时,对文学本质问题采取了实用理性的态度,而不是科学主义态度。他在讲话《结论》部分的开篇处着力批驳了从本本出发的文学观,主张从实际出发,文学为现实服务。“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3]这种阐释策略,回避了苏联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论界定,暗中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他找到了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和马克思实践论的平衡点,增强文艺思想的合法性依据。而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便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以及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纪梦想。
其次,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修正,突出强调文学的革命理想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六个更”实际上突出了文学的理想性,用革命理想主义的神圣光环来矫饰和美化现实,以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情怀,从而推动革命进程,使文学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思想避免了苏联文学理论二元体系的内在矛盾,让文学真实性服务于意识形态性。明确提出“以写光明为主”的创作指导思想。文艺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改造,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乐感文化”精神、大团圆模式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式的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文艺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大众化”文艺思想,并且主张民间化的文学路线。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具有反资本主义、大众化、集权化、道德化以及大众崇拜等特征。厌弃西化路线,终其一生苦苦追寻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他带有浓厚的大众意识,不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依靠农民,走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依赖于人民大众的价值观。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主义对于那些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关的组织和制度都很厌恶,这一点与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对专业化分工的偏见,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大规模集中化组织形式的反感,对所有官僚主义现象的坚决反对态度,以及对于正规高等教育的不信任”[5]革命民粹主义倾向,注定了中国革命文艺政策的大众化、民间化路线。
的“大众化”思想有两大要点。其一,创造性地把“大众化”口号具体化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阐述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第一,普及是基础,提高是指导,“……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这实际上是要消除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区别,使二者统一于工农兵文学。第二,先普及后提高,“对于他们,第一部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这实际上是要高雅文学为工农兵文学作出牺牲。第三,屏弃知识分子书写传统,主张在工农群众的俗文学(普及)基础上创造新的雅文学(提高)。“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这实际上要避开古今中外已经有的高雅文学遗产,另起炉灶,从工农兵文学中产生新的高雅文学。其二,大力提倡“民族形式”,走上了一条民间化路线。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这段话并不直接针对文艺界,但对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引发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在《讲话》中对此次大讨论作了总结,批评部分作家“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确定民间形式为大众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又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1而大众化、民间化的提出,并不代表民间立场的崛起,。只是希望通过民间舞台来演出革命意识形态的大戏,实质上是国家主义对民间立场的借用和转喻。必须指出,苏联文学理论、文艺思想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任务的完成,这是不能否认的。同时,由于理论本身的偏颇以及历史条件的变化,不能适应文学的现展,产生了“左”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理论由合作到分裂、对抗
建国以后,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有了一段合作时期。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形而上学传统,建立了严整的逻辑体系,理论性较强。因此,在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文艺思想继承了中国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思辨性较弱,但更适合中国国情,更具有政策实用性。二者互补,共同主导着中国文坛。它们共同的对手是五四时期引进的现代西方文学思想。因此,自建国以来,连续发生了文艺领域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主流的苏联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联手对残存的西方文学思想进行了清除。这个时期,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它们之间的分歧被掩盖了。
但是,苏联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分歧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分歧就有可能突显并且扩大,发生冲突和对抗。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自苏联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以来,中苏的政治分歧扩大为两党、两国之间的分裂,终于演变为中国开展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文学思想领域的分歧也逐日公开化,成为政治斗争的缩影。1958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取代了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标志着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取代了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以“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为副;而前者提高了“浪漫主义”的地位,与现实主义平起平坐。实际上,在苏联文学思想的语境中,所谓“现实主义”被阐释为现实性、客观性,而“浪漫主义”被阐释为理想性、主观性,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一种曲解。实际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它反抗工具理性和现代工业文明对激情、自然的扼杀。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二次反叛,它揭露、批判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灾难以及人性的堕落。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两结合”都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无关,它们只是新古典主义的不同形式。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保留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强调客观性、真实性的基础,而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即“两结合”更突出地强调了文学的理想化,进一步冲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微弱的客观性。“两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必然把文学导向粉饰现实的歧途。
“两结合”的提出仅仅意味着中苏文学思想的分歧初露端倪,而后的“反修”运动才正式揭开了双方斗争的序幕。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理论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化为对抗。文艺思想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合,而把尚保留有认识论和人道主义倾向的苏联文学理论当作“修正主义”批判。1960年初,《文艺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动员在文艺界开展反修斗争。《文艺报》社论称:“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它的主要表现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唯心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宣扬个人主义来反对集体主义;以‘写真实’的幌子来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以‘艺术即政治’的诡辩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创作自由’的滥调来反对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领导。”1以后,中国文艺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思
想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时期,并发展为对“文艺黑线”的斗争,也就是把“三十年代文艺”、“十七年来的文艺”与“现代修正主义文艺”联系起来,编织成一条“文艺黑线”。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批判“黑八论”,所谓“黑八论”是“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离经叛道论”等。可以看出,这些受到批判的文艺主张基本上是属于苏联文学理论,特别是“非斯大林化”以来的苏联文学理论。紧跟文艺路线,而又有苏联文学理论背景的周扬等正统理论家受到批判,只有从中苏文学思想之争的角度才能理解。与苏联文学理论分家,在“”中偏执化的主流文艺思想走向极端,它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遗产打成“封、资、修黑货”,使中国文学完全封闭;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大批文学作品被打成“小说”,提出了包括文学领域在内的“全面专政”理论;新古典主义演变为伪古典主义,所谓“样板戏经验”(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等)成为文艺的唯一指导原则;“工农兵文艺”的极端化导致文学创作的毁灭。总之,在革命战争中诞生的革命文艺思想,在和平时期没有及时加以调整,走向偏执化,并且与苏联文学理论发生对抗,给文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苏联文学,依然有像肖洛霍夫那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且出现了像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异端作家,他们拒绝加入国家大合唱,拒绝廉价的颂歌,保持着心中的那份真实和真诚,即便遭受镇压、监禁、流亡亦无悔。他们给苏联文学留下了辉煌的遗产。而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建国以后的文学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成果。其内在原因是,苏联文学理论是二元结构的理论体系,不仅有意识形态论,还继承了西方认识论的思想传统,还有人道主义的影响。这样,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功能和真实性追求相互制衡,为文学创作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而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形式则是意识形态一元论,取消了文学的真实性、客观性,也抹杀了文学的人道主义因素,因此没有给文学留下最足够的生存空间。一元论的文艺思想虽然有助于加强革命宣传,发挥文学的政治功利作用,但由于产生了“左‘的倾向,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异端思想存在,最终把文学桎梏在偏执化的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
参考文献: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美]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P60
1参见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年创刊号。
1《文艺报》1969年第一期社论《用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