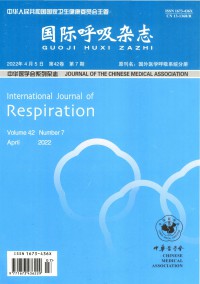国际政治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国际政治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战后几十年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特别在冷战格局和平消解后,传统理论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解释力日渐式微。文化这一国际关系的传统变量在经受了长期忽视和掩盖后,其作用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传统理论的视野中脱颖而出,成为探究国家行为、对外政策、国际安全等国际关系问题的第三向度。研究国际关系中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主义也成为同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文化、规范与认同,集体认同既是文化解释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建构作用的重要媒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从文化的视角几乎可以诠释出一部新的国际关系史。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主权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Politics,Vol.50,No.2,
January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Berger,“Norms,Identity,andNationalSecurityinGermanyandJapan”,inPeterKatzanstein
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Katza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c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inInternational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96,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RobertCohaneandLisaMartin,“ThePromiseofInstitution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主权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1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securitycommunities)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p.11—18;Richard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p.428,430;Rochard
NedLebow,“TheLongPeace,theEndoftheColdWar,theFailureofRe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主权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主权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00—401;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Mas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
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11;Richard
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
虽然都是保护成员安全的安全机制,但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在本质上比集体安全优越。集体安全具有强制性,是通过外在的威胁和制约实现世界的和平。但是,多元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自愿、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之上的,不具有强制性,主张通过内在的认同和自律实现世界的和平。集体安全体系内可能会有“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但是在安全共同体内不会有任何国家成为挑战体系的“麻烦制造者”。在安全共同体中,所有国家都认为战争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且这种想法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集体认同的程度即不同等级的文化认同决定国家间关系的类型和国际安全的存在程度。根据温特的分析,只有在以朋友关系界定的康德文化下,国家间才能真正建构积极的集体认同关系,实现充分的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