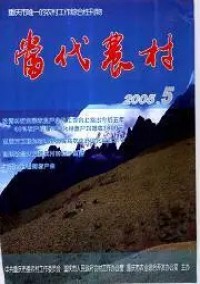农村权力结构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村权力结构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提要]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的目标,就是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同时,完善村党支部的领导机制;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直接公开的竞选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在共同的民意基础上建立村委会与党支部职能协调的制度化机制。[关键词]村民选举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党支部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Kelliher),1997年他在《中国学刊》(TheChina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言论更加稀少。最近一期《乡镇论坛》的一组专门讨论村支两委关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当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还要不要党政分开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3]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人,有的认为,如果硬要搞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不仅很难保证村民选举的公平与竞争性,而且将导致党的基础力量的损失。[4]有的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认为村主任与村支书,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同、性质与职责不同、工作重点与工作方式不同、制约机制完全不同,如果两个职务所肩负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会使“一肩挑”的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5]还有的人强调法治原则,主张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并反问到:“全国农民都在自己选出的村委会带领下依法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难道不正是我们党的最大愿望吗。”[6]
在赞成或支持党政合一原则的阵容中,有人从实践体会的好处罗列了“一肩挑”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提高了村委会的地位;既增强了村民选举的竞争性,又加强了村支两委的团结;既化解了干群矛盾,又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办事效率,等等。[7]还有的人认为,“党政分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理念有必要改变,实行“两委合一”为中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深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其潜台词就是抛弃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最好的权力格局是村主任都由村支书兼任,村支两委高度重合。[8]
显然,这场有关村级党政关系的争论,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争论焦点——党政能否及如何分开的继续。既然有人提到“党政合一”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深化摸到了一条路子,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一肩挑”故事,将会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摹本?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都不能小视目前的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起码,就目前的争论来看,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政改原则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动摇。
二、村民选举后的农村权力结构
在回应上述争论之前,有必要廓清村民选举后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实际状况,以便从理论上把握农村党政关系的实质。
邹谠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个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宏观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能主义政治就是建立在一个总体性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9]“党核心”具有纵横穿透力,在这种政治穿透的作用下,中国的各级权力组织都具有同构性,即所谓“组织对口设置”、“上下碗口一般粗”等等状况。在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农村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妇女会、青年团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农村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农村党政关系是政权层面的党政关系的缩影。因此,农村党政关系的重建无疑对宏观政治结构的重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在实行村民选举以前,农村权力关系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改变了村委会权力来源的基础,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渠道与党支部出现了分野。如果党支部的权力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性质,那么村委会的权力依赖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村民授权,村民选举就是这种授权的制度化渠道。这就从根本上促使农村公共权力转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说到权力结构,必须考察权力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即权力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对比。[10]从这些要素结构分析来看,村委会与党支部是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变化:从集体垄断到多元配置
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所以得以巩固,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集体垄断。在全盘集体化中生活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政治上也就谈不上自治权了。
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非集体化改革,实质上是打破经济资源集体垄断的过程。非集体化的过程,无论是美其名曰“藏富于民”也好,还是恶其名为“集体空壳”也罢,必然是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的集体控制向多经济主体控制模式的转型。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粮食和现金的处置权,也就意味着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依附于村集体或村干部。反过来,村集体或者村干部要靠从村民手中提留统筹才能运转或生存。村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当然,潜在的权力资源要转变成权力者可以动用的资源,需要有一个资源提取的过程。就权力资源提取的合法性来看,村委会有资格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公私混合经济中提取经济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集体经济。[11]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是党支部权力的经济资源的唯一来源。因此,集体经济的强弱与党支部权力资源的多寡有直接的关联。显然,弱集体-强私营的经济结构使村委会占有的权力资源有可能优于党支部,导致“党弱村强”格局的出现。然而,在农户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村庄,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经济资源。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12]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及其提取方式?飧龇矫妫共荒苋嫒鲜杜┐宥峁沟淖纯觯剐枰疾烊丛椿蛘呷Φ暮戏ㄐ晕侍狻?/P>
第二,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渠道。就程序民主来说,治者之权必经被治者认可才具有合法效力。治者的权力主要有两种来源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村民选举。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农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是上述的程序民主原则。当村民发出“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的诘问时,他其实是质问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他们的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会质疑村民选举的意义,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13]
其实,村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要从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衡量。党支部的基本政治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村党支部的权力并不取决于选举(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扩大的支部选举如“两票制”),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正确,也就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本村范围得以正确地执行。因此,党支部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村委会选举也还没有发展到选政策的高度)。[14]因此,村委会对党支部领导的服从,实质上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服从,而不是听命于村支书的个人意志。如果一个党支部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么它既缺乏程序合法性,也失去了规范合法性。那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尽管成天把“党的领导”挂在嘴上,其实是利用“党的领导”这个金字招牌来掩盖其贪桩妄法的行经。严重的是,这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所耗损的正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权力影响力及其变化
权力影响力是权力强弱的综合体现。对这种影响力的衡量,需要经验观察才能判断。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权力影响力的要素主要包括:1)组织吸纳能力,即吐故纳新、容纳社会精英的能力;2)社会动员能力,即宣传、发动、取得民众支持的能力;3)制度监督与组织自控能力。
从现实观察来看,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不少农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在村落中的影响力削弱了,一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削弱了;二是村里青年人的入党积极性下降了;[15]三是作为党支部的外围组织或者“助手”,如共青团、村妇联等也几乎名存实亡。[16]据有关部门于1995年的调查估计,全国大约有10%的农村党支部处于这种状况。[17]这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对1亿左右农民群众的政治影响!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能力弱化的原因,固然同权力资源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源是党支部组织建设没有根本解决“四个化”的问题。所谓“四个化”,就是农村党员队伍的老化、党性观念的淡化、思想观念的僵化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在近期全国农村学习贯彻“三代表”思想的活动中,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国内外许多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问题的学者,大多认为村民选举加强了村委会的权力,提高了村委会的影响力。[18]就笔者的经验观察来看,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原因在于,定期的村民选举使村里的各种精英可以通过竞争而进入村委会。起码,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村民选举制度既提高了村委会吐故纳新的活力,也能够通过预期选举或启动罢免程序来保证村民对村委会的动态监督。这种动力机制无疑有助于村委会影响力的提高和巩固。图1是笔者对村民选举后农村党政关系类型的一个经验分析框架.
先看“党强村强”的A型结构,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合作的制度机制。这种党村共强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理想模型。第二,“党弱村强”的B型结构,就是村委会主导村政事务,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其基本特征是,村委会控制了村庄大部分权力资源,村主任是村政事务的实际责任人,也是上级任务的主要承当者。党支部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则在于“自毁长城”。第三,“党强村弱”的C型结构,就是党支部的组织吸纳力、社会动员力和政治监控力都比较强,党支部的群众威信较高,受党支部支配的村委会只是个执行机构。这种权力结构一般具有“行政化”的特征。[19]这种结构又同乡镇“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最后,“党弱村弱”的D类型,就是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软弱涣散,都不能按照制度规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村往往既是组织“瘫痪村”,又是经济“空壳村”。
第四,权力制度规范的差异:法与政策
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制度规范各有特点。《村委会组织法》是村委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其他相关法律也是村委会组织行为规范的来源。其次,各地农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办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等,既对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也是村委会的具体行为规范。而农村党支部主要依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运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支部的行为规范主要来自不同时期的党的政策,它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也因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法的相对稳定性同政策的相对灵活性,这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既导致了村支两委的规范差异,也导致了村支两委工作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村支两委及其负责人角色协调的制度条件,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内在一致。如果政策与法律打架,投射到村支两委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关系紧张。这时,村支两委的权力冲突,反映了法与政策的内在矛盾。
三、农村党政关系的制度化调整
无论是坚持“党政合一”的立场,还是坚持“党政分开”的观点,似乎都不否定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这就是党的领导同村民自治或者说村支两委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坚持“党政合一”或者“一肩挑”的人,相信村支两委由此能够更加协调一致;而坚持“党政分开”的人,则认为更多地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对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有利。如果党支部不陷入具体事务,就可以腾出手来抓大事。
笔者以为,农村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宏观党政二元权力格局在农村社会的延伸。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既不能以党代政,使得村民自治如同虚设;也不能以政代党,把党的领导迷失在繁杂的事务工作之中。然而,无论进行何种制度设计,都必须在解决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解决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把村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机制一同纳入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村民选举的实际情况。民政部党组对1999年全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有个评价:村委会成员的构成比例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党员比例高、致富能手高、文化程度高、平均年龄低)。[20]广东民政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说,全省10多万当选村干部中,中共党员占77%,党支部书记成功竞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占53%。[21]这两个数据说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获得了村民群众的信任投票,村民选举的党员和非党员村干部,都有责任、有能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定任务。各地“一肩挑”的比例并不平衡,比较高的如广东的顺德、高州和郁南等市县,“一肩挑”的比例高达90%,[22]在山东省威海市,村支书当选为村主任的比例是65%。[23]在河北省隆化县,在村委会第五届换届选举中,村主任是村支书的比例为4.7%,而村主任是党员的占57.2%。[24]
其实,村支两委交叉兼职很普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坚持了“党政合一”的原则,而是村级干部职数的限制,不得不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结构。说交叉兼职减少了干部职数的论点也不成立,因为由村财政负担的干部职数基本上是不变的,维持在5-7人左右。实质的问题是,“村支两委”的人马如何产生的,是村民选举的人占多数,还是上级任命的人占多数?更为关键的是,村级混合班子的“班长”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这就涉及到“一肩挑”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村民选举的制度同时导入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干部选择,那么“一肩挑”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如果把“一肩挑”作为出发点,就有可能硬性推广这种模式,导致操选、霸选、逃选等不合法或不当行为的出现。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农村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纳入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制度措施。具体的做法可概括为二种模式,一是“两票制”选村支部,二是“二选联动机制”,[25]即“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与“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两种联动形式。例如,在广东省首次实行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估计以“二选联动”实现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及交叉兼职的农村,占全省农村的50%以上。[26]这种建立在直接选举基础上的交叉兼职结构,使村支两委避免了权力冲突,增强了村级组织的整体能力。
“两票制”发端于山西省河曲县。这个县在1991年初实行“两票制”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党支部权威不足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经过不断完善,“两票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了预期作用,山东、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广东等省市正在结合本地情况借鉴推广这一经验。[27]1998-1999年,深圳龙岗区在广东率先引入两票制选村党支部,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8]并把“两票制”提升到镇长选举的制度改革上来。[29]“两票制”的实质,在于支部建设中导入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从而扩大党内民主,使村民群众在支书和支委的人选上开始拥有发言权。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创新,那么其本质就是在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在保持党支部权力自上而下性质的同时,为党支部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提取权力的信任资源的渠道,从而巩固和维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村民信任投票的多寡就是这种合法性的量化形式。因此,在推行两票制的过程中,越能提高和保证村民信任投票过程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也就越能提高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河曲“两票制”经验被许多省市认同的根本原因。
“两票制”使村党支部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有助于解决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问题。[30]这种制度化途径也让村民有了监督村支书和支委成员的权力,即如果凭借村民信任投票上台的村支书不为民谋利甚至蜕化变质,那么村民在下一次的信任投票中就能把他赶下台。
而“二选联动机制”似乎更为直接有效。说它直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在职的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如果当选了,在获得群众投票的基础上一身二任,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的权力争端。二是如果当选的是一个普通党员,那么由于他的民意基础强于在职的村支书,他也就有理由出任村支书,实现“一肩挑”,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两张皮”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无论是村支书竞选成为村主任的“一肩挑”,还是当选村主任被推选为村支书的“一肩挑”,都是村民直接选举的结果。如果颠倒过来,预先圈定在职村支书为村主任,就不可避免会滋生操纵选举等违法行为。
这样看来,解决农村党政关系问题有三种制度化途径,即“两票制”、“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三种制度化途径的实质就是把村民直选的制度机制纳入了村支两委的组织建设。那么该如何运用这三种制度化机制呢?按照简便有效的标准,这三机制的启动次序是:首先启动“从支书到村主任”的机制。这就要求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竞选成功者继续保留村支书职位,对于那些不敢参与村民选举的村支书,党内应该撤换。其次启动“从村主任到村支书”的机制,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大胆参与村委会选举,当选的村主任以其得票最多,既成为村委会主任,也成为村党支部改选的首位候选人。第三是启动“两票制”,假如当选的不是党员,那么就应该随后实行“两票制”选村支书和村支部,把无能的村支书选下来。为配合这样的制度机制,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任期应该基本保持一致。
总之,村委会与党支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维护村民权利方面可以齐心协力,这就有条件也有动力以村民选举的制度化机制来协调、改善村支两委的关系。
四、结论
农村的党政关系实质上是二元权力结构,村支两委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征,但通过引入直接选举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协调两者的权力关系。
村民直选制度强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地位,为村委会自上而下地提取民意支持(民主授权)提供了合法渠道。尽管乡镇党委及村党支部有办法控制甚至操纵村民选举,但这种做法已经失去合法性。在村民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微观背景下,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由此能够从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两票制”、“二选联动机制”就是提升党支部权威、协调村支两委关系的制度化机制。
在农村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协调党政关系的制度化机制,既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双赢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确实,我们似乎还看到,一个与人民群众有鱼水关系传统的党,也有必要着手建构这样的制度渠道,使人民群众清晰地表达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