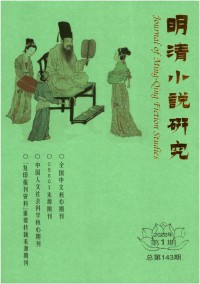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及意义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及意义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者将全国市场网络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既吸收了施坚雅理论的层级概念,又代之以更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网络论。文章特别强调: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明清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经济发展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入侵后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
【关键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正文】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日本学者致力较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施坚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3papersJournalofAsianStudies,24,1—3(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nalEconomy: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80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做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八大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注: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个等级(前引书第158页),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流通枢纽城市的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90%(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与长江合计,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分类康熙25年雍正2年乾隆18年嘉庆17年
全国关税总额122.0万两151.5万两459.6万两481.0万两
运河诸关税额61.6万两61.4万两150.5万两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50.5%40.6%32.8%29.1%
沿海诸关税额18.2万两20.3万两103.2万两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14.9%13.4%22.5%36.9%
长江诸关税额37.3万两48.7万两114.6万两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30.6%32.1%24.9%28.0%
三者合计117.1万两130.4万两368.3万两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96.0%86.1%80.2%94.0%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2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粮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以上,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不如明代,该关税收大体保持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濒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故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2万余两,是全国八大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当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注:雍正《北新关志》卷三《禁令》。);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000余两,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西藏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八大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两,天启时为57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清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在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注: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似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总计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2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嵩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州县税额(两)占总额%
福山县12123.59628.67%
即墨县8736.55220.66%
胶州6071.46914.36%
掖县3602.238.52%
海丰县2025.37354.79%
利津县2018.044.77%
黄县2011.4054.76%
荣成县2004.2194.74%
蓬莱县1503.1083.56%
文登县904.232.14%
诸城县502.691.19%
海阳县402.440.95%
宁海州304.310.72%
日照县71.0280.17%
总计42280.69100.0%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而以福山为最。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州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而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农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等地的集市也在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22000—25000个,清末可能超过30000个(注: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贩运路线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注: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乃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禁止→放任→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开设的十几个主要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天津、牛庄、汉口、烟台、九江等,在开埠之前商业均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它们或者是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或者是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但一些近代史论著对它们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往往评价过低,从而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如:近代史著作中一般都把天津开埠以后的发展表述为从一个漕运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而实际上天津的这一转变过程早在清代前期已经开始了。对上海的定位也存在类似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近代史论著将上海开埠之前描述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以后的飞速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实际上在乾隆—道光年间就已经奠定;另一方面,由于“独口通商”政策的影响,也扼制了它本来可能的更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过程是在开埠以后实现的。
经济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无疑渗入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动力。1840年是一个政治性的界标,至少经济史的研究不应拘泥于这一界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