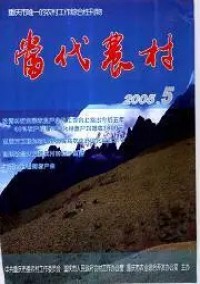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又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造成了农村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的功能,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撤地;强县;精乡;实村
改革开放27年来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职责交叉、人员臃肿、结构不合理、财政负担重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尤其是最近七八年来,“地区”一级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和服务明显下降。这与党管农村工作的一贯原则,即“地、县两级要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1](p25),是极为不适应的。同时,乡镇一级政府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又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扩张的压缩、且缺乏必要的财政基础,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2]。前不久,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3]。这预示着中国政府改革将由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了“减少层级”的行政体制架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一级的行政建制,强化县一级的政府功能,精简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和保障村民自治必要的财政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一、地区一级建制“弊大于利”应当撤消
依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地方行政建制共分为3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但在实际运行中,原先只是作为省级派出机构的“专员公署”,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实体型的“地级市政府”,且大多数省份也都实行了“市管县”或“市管市(县级)”体制。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地级行政区共有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占85%,尚未“撤地设市”的仅有50个(包括17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只占15%[4]。这种绕开宪法任意增加地方行政建制的违法行政行为,不仅造成了省、县之间的层级模糊问题,而且还有不少地级市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现象”。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了,目前我国“地区”一级正在演变成为一架养尊处优的“腐朽国家机器”。以1个中等地级市为例,仅市一级就拥有厅级干部30多人,处级干部200多人,科级干部1000多人,机关工作人员一般都在10000人以上,每年需要行政经费支出5亿元左右[5]。据初步匡算,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机关干部人数约在300~350万人,所属事业单位职工人数约在550~600万人,全部财政供养人员约在900万人以上,一年消耗掉的行政资源估计在1300~1500亿元之间。
根据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般原理,“作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机构,政府的各种行政支出只能从财政收入中支付,政府的规模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财政供给能力;如果在一个财政供给能力很低的地区,仍然保留着庞大的政府规模,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而不是有利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6](p353)。譬如,河南省信阳市和驻马店市,这2个传统农业大市过去统属于原信阳地区管辖(1949年5月至1965年7月),当时共有19个县级行政区(不包括泌阳县),总面积达到3万平方千米,总人口接近800万人,干部总人数为65410人[7](p322),地方财政收入为19950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8000万元,基本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8](p10)。但自1965年7月起,驻马店从信阳分离出去,成立了新的地区行政公署。从1965年到2004年的近40年,信阳地区(1998年8月“撤地设市”)管辖的罗山县、息县、固始县、淮滨县、潢川县、光山县、商城县、新县、信阳县、信阳市和驻马店地区(2000年10月“撤地设市”)管辖的确山县、遂平县、西平县、上蔡县、汝南县、平舆县、正阳县、新蔡县、泌阳县、驻马店市,“官僚机构竞相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即著名的“帕金森定律”)[6](p87),远远超出了地方行政资源的承载力,长期主要靠吃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变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几乎失去了“造血功能”。
据统计,1952年10月,潢川、确山这2个专员公署合并时,信阳地区干部人数为26627人,官民负担系数为1:174;而到1965年7月,驻马店、信阳“分家”后,留在信阳地区的干部人数为44392人,官民负担系数一下子提升到1:95。直到1995年底,原信阳地区干部人数已达到了10.8万人,官民负担系数为1:48[7](p322~324)。特别是从1998年到2004年的短短6年,信阳市财政供养人员由18万人猛增到25万人,官民负担系数也由1:43提高到1:31;但同期的地方财政收入仅由8.4亿元增长到12.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却由15.37亿元增加到40亿元,地方财政资金缺口由“撤地设市”前的1倍扩大到了2.3倍。目前,驻马店市财政供养人员已由1965年的2.1万人增加到24.5万人,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3.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竟高达37亿元,地方财政资金缺口也接近了2倍。另据调查,信阳市乡、村两级负债总额高达15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在600万元,平均每个村负债在100万元。如该市的息县近5年来,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别为6471万元、11622万元、14913万元、22321万元、28648万元,占到了全县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37.5%、60.4%、45.5%、65.4%、72.7%。总体而言,像信阳市和驻马店市这样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旦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恐怕连维持政府自身的正常运转都会成问题,更不要说搞什么地方经济建设项目了。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方兴未艾。“下放权力,扩大公民参与地方行政管理,使地方行政管理更加贴近公民,贴近实际,是西方国家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普遍的做法”[9](p281)。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规模大小的确定,主要取决于财政供给能力的强弱。即对那些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地区,国家保留其适度扩大或缩小政府规模的自主权,允许制定一些特殊的“弹性政策”;而对那些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国家也不能因其拥有强大的财政供给能力,任其随意扩大政府的规模,要制定一些“强硬政策”予以遏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的西方国家将地方行政管理纳入市场竞争当中,如果有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及时有效地为公民服务,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私人企业能够很好地提供这一服务,那么中央政府就将停止对地方政府这一职能部门的拨款,而将相应的款项拨给能够为公民提供良好服务的社会团体或私人企业”[9](p282)。总之,西方国家主要不是靠增加地方行政建制和扩大政府规模去整合社会,而是通过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去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留下的空白地带,使之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但在中国,时至今日人们仍很少关注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尤其是像“地区”一级这样的模糊行政建制,其管理幅度与民众直接受益程度呈反比,而其行政成本又与地方财政资金消耗呈正比。这是影响和制约我国行政效率整体提高的根源所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最多延伸到省一级)和目前正在开展的乡镇政府机构,都把地区一级当成了“改革盲区”。因此,中国下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重点和突破口是“减少政府层级”,即撤消地区一级的行政建制,实行市、县分置(地级市一律改为县级建制),逐步从“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建立和完善“省直管县”或“省直辖市”的地方行政管理新体制。
二、县级行政建制“地位特殊”应当强化
不管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现阶段,“县”作为地方行政建制中最为稳定的一级,“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团粒结构的稳定社区,能够在任何国家制度下,都以不可轻易分解的行政实体而发挥作用”[10](p182-183)。中国自秦朝正式确立“县制”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具有区域经济上的内部关联性,社会、文化、历史语言上的同一性,交通网络和城镇体系上的完整性,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上的相似性等等特征。它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治的安定、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安康等,始终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功能,其地位特殊且作用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也保留了一些县政区,譬如日本的1都、1道、2府、43个县都属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之下设立市、町、村);美国50个州之下保留了3137个县,也都属于二级地方行政建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9亿农民和56个民族的人口大国,“县制”作为最古老、最完整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不可能在一片“县”改“市”的热潮中消失,也不适宜把“县域”都改成所谓的“城市社区”。首先是它的覆盖面广。截止2004年,全国县级行政区共有2862个(其中,包括852个市辖区、374个县级市、1464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2个特区和1个林区),县域面积为874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94%,居住着9.1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1%[4]。其次是它的衔接性强。县域处在“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特殊位置,是城乡经济文化交流的有效对接点。目前,我国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60%左右,成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生长点、突破点、结合点。最后是它的综合性高。县域内包括了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企各个方面,而“一级完整的行政建制,其核心内容就是具有一套健全的政权机构及其合法行使权力的活动空间,包括地理范围、周边界线、一定水平的政治经济中心等”[9](p265)。总之,“县制”在我国具有不可替代性,强化县一级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目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我国大多数省份已形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和以县城为中心的农村经济圈,且形成了县城至省城数小时的公路交通网。这些都为我国实行“省直管县”行政体制创造了现实基础。但是,由于我国一些县级行政区划不合理和机构设置重复、分工过细、部门林立、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等,造成了行政资源配置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譬如,河北省与湖北省行政区划面积都是19万平方千米,但前者比后者竟然多设置了70个县级行政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再如,目前我国不论县域面积大小或经济实力强弱,县级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都是千篇一律的,于是出现了“庙小和尚多”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现象。截止到2004年,全国20万人口以下的县还有720个(其中10万人口以下的县314个),有的县一年财政收入上亿元、甚至十几亿元,有的县一年财政收入却只有二三千万元,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基本是一样多,结果造成了“行政权”与“财政权”极为不相匹配。就整体而言,目前县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但其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县政府几乎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尤其是近年来,地级市与县(市、区)之间的“事权”、“财权”划分相当模糊,“大市”政府垄断了辖区内的骨干工业企业和主要财政收入来源,造成上下级的利益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以至出现了相互扯皮、相互推委的现象。县、区政府领导经常抱怨说:“市里有好处就争,遇到矛盾和问题时又往下推”。因此,下一步应对市、县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省、县之间的“事权”与“财权”进行科学划分,通过建立和完善“省直管县”或“省直辖市”行政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把省级政府部门的大量行政审批权直接下放到县一级,促使县政府真正成为“独立、完整的政府”,逐步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乡镇一级政府“必不可少”,但应精简机构和人员
“乡镇”是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它作为介于县、村之间的中间组织,体现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权关系。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指出,“乡镇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类集聚就能自行组织起来的惟一联合体”[11](p66)。但在中国,秦朝至清末一直实行“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行政体制,“乡”的建制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时至今日,我国“乡镇”一级仍然是“党政权力高度一体化和政治、经济、社会与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12]。尤其是近几年,我国采取“县政权取实,乡政权取虚”的简单做法,大规模地“撤乡并镇”,使乡镇政权处于非稳定的状态。譬如,1985年到2004年的16年间,全国乡镇数量由91138个下降到37334个,共减少了53804个,甚至比“一大二公”的数量还减少了17018个[13]。预计到2010年,中国乡镇数量将保持在3万个左右[14]。
根据政治学的一般原理,国家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得越深坏处越多,将使基层活力泯灭、发展停滞;但地方行政区划规模过大,又将导致“政令不通”和行政效率低下。因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都是从便于行政和便于居民参与本地管理出发,综合考虑了历史、地理、民族诸因素,根据一个基层行政单位能否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确定的”[15](p341)。如美国现有19429个小市镇,16504个乡,35052个特别区,13506个学校区。这些都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基层政府组织,但其辖区面积大小不一、人口也多少不等。像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乡,有的多达4万人,有的还不足300人。而纽约州的小市镇,有的面积仅为1平方千米,有的达到了几百平方千米,人口从百人到几千人不等[16](p1041~1042)。再如,法国现有36413个市镇,平均面积仅为14平方千米。其中,市镇人口在10万以上的37个,2万人以上的334个,1500人以下的3.5万个,且大多都在300人左右[17](p397~398)。据1996年中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乡镇面积为189.92平方千米(其中乡为230.22平方千米,镇为122.48平方千米),平均每个乡镇人口在2万人以上[18](p366)。即使这样,我国从1998年开始又掀起了新一轮“撤乡并镇”的高潮,全国平均每天都会有4个乡镇悄悄的消失了。可见,“只要乡镇自由还未成为民情,它就易于被摧毁;但只要它被长期写入法律之后,就能成为民情的一部分”[11](p108)。
总之,“精乡”就是把乡镇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权规范到合理的空间,使之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但由于我国对乡镇建制规模、管理层级、治理能力、功能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缺乏整体设计和法律保障,同时又受制于国民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民义务教育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制约,最终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长期处于被动的施政状态。而当前我国开展乡镇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就在于,进一步保持乡镇政权名称的固定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稳定性,人员编制的合理性、政府运行的规范性和法律约束性,使之真正成为直接面向9亿农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组织。这是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四、“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应当充实
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聚村而居”。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19](p9)。正因为这样,“村庄民主”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基础工程。正如同志曾经指出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20](p202)。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同志进一步指出了,“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最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要靠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团结和带领农民去落实,要靠农村基层组织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去实现。
但从实践上看,由于村级组织既不是行政主体,又缺乏必要的财政基础,它很难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可能会侵犯农民的利益。因此,通过“村民自治”或通过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重新把农民引入到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组织中去,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但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着“甩包袱”的思想,县、乡政府通过“管人、管账、管工资”的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村级组织的行政管理与控制,使村级组织“行政化”和村干部“公职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这不仅动摇了“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和存在基础,而且也使村级组织正面临着将成为“附属性行政机构”的危险,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村出现了“无人主事、无钱办事、无章理事”的混乱局面。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量由101.3万个减少到65.8万个,村干部人数也由455.9万人减少到259.2万人[21]。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税费尾欠清理与县乡财政资金“刚性结算”双重挤压下的资金困境,使村级组织缺乏必要的公共行政经费。加上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尚不明确,一些地方政府推卸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甚至把自下而上向农民收取的各种集资款和自上而下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全部用于政府自身的正常运转,最终导致乡村社会没有了一些生气。尤其是“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的乡政权力既可能是村治权力成长的有力推动者,又可能是它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说,在村庄层面,村庄精英和村民究竟能拥有多大的自主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乡镇”[22](p122)。这使得“村民自治”的活动空间经常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扩张的压缩。总体来看,我国农民目前正处在剧烈分化、融合、重组的状态之中,其突出特点是高度分散化和无组织化。
因此,我国近期应把地方公共财力重点向村级组织倾斜,首先确保村干部报酬按月兑现,并对村级组织提供必要的公共行政经费开支,以便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从长远发展看,我国应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为农民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社会养老、基础设置建设等提供资金的支持。当然,迄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为8~9亿农民提供财政补贴以保障这部分人收入较快增长的先例,仅靠国家财政补贴方式尚不足以改变农民自身发展的缓慢进程。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村庄是生产性的”。只要真正能够体现出“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让农民自由、自主、自治的活动,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组织部.农村基层干部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
[2]张新光.论中国乡镇改革25年[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16~19.
[3]张占斌.强县扩权与省直管县:析中国政府层级改革两思路[N].学习时报,2005-08-04(01).
[4]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5年)[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
[5]许峰.取消地级市入视野“省直管县”将有试点[N].南方周末,2005-09-15(04).
[6]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信阳地委组织部,党史委,档案局.信阳地区组织史资料(1925~1987)[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8]信阳市统计局.信阳50年[Z].1999.
[9]李贵鲜.公共行政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中国政区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1][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1998,(5):37~51.
[13]张新光.论我国乡镇的建制规模、职能定位与机构设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09):272~275.
[14]李卫玲.乡镇体制改革不能“一刀切”[N].国际金融报,2005-10-22:(02).
[15]刘君德,冯春萍,华林甫,范今朝.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M].上海:华东出版社,2002.
[16]王力:乡镇长手册[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17]秦德占:乡镇干部工作手册[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18]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0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1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1]李培林.重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J].人民论坛,2005,(10):28~29.
[22]金太军,施从美: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