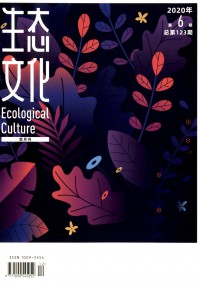文化史论文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文化史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戏曲艺术教育
一些高校开设了戏曲音乐欣赏课,有的还成立了大学生戏剧团。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社会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对戏曲不感兴趣,忽视戏曲知识的学习和戏曲音乐的渗透。戏曲课不仅开设的少,而且形式单调,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戏曲艺术的影响力,尚不能将戏曲融入校园文化。校园文化作为时代先锋,对戏曲艺术的接纳程度直接影响了未来戏曲的走向,也渗透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原国家领导人总书记曾多次号召振兴京剧事业,这是发挥戏曲艺术教育功能、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提高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生对戏曲艺术的认识,不但可以增长学生这方面的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陶冶学生的情操、振奋民族精神、提高艺术素质,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是高校艺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戏曲艺术教育对振奋民族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戏曲是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中国的戏曲艺术在世界艺坛独树一帜,是融表演、演唱为一体且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艺术,是综合各种艺术成分浑然一体的。唱、念、做、打是戏曲的突出特点,行腔转调、发音吐字,都有一定规矩和要求,而做工的手、眼、身、法、步,都要经过专门的严格训练,念白的韵白和口白均要有音乐性,武打要干净利落、稳妥准确、轻捷灵便。其表现手段的程式要求更是严格,唱、念、做、打和音乐伴奏以及服装、化妆、布景、道具等都有一定格式。它集中国各民族文化之大成,是经过无数艺术家继往开来不断创新积累的结晶,是博大精深的艺术体系。戏曲文化的发展史体现了中国民族艺术文化发展过程。所以,高校艺术教育开设戏曲艺术课,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民族民间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能促进学生学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积极性。
目前高校大多数学生喜欢流行歌曲、摇滚乐等,有些对西方音乐也颇有兴趣,然而对中国音乐却提不起兴趣特别是对我国戏曲艺术知之更少。不知道“徽班进京”、“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是什么,对千百年传唱不衰的戏曲剧目与代表人物、中国的戏剧创作大师缺乏了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也在提高,越来越认识到了发达国家所重视的通才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国家以立法或者国家计划的形式把戏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规范化,而我国这种现状与当前艺术教育的要求极不吻合,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来抓。
戏曲走进高校艺术教育的课堂是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通过戏曲艺术教育,使学生认识、掌握戏曲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扬长避短,发扬光大,使更多学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在这些遗产中,戏曲则是独具风貌的重要艺术形式。要让学生知道,这里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表演,有长久传唱不衰的唱段,还有传播范围极广的民间传说。这些必将激起学生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因此,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高校学生进行戏曲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需要。
二、戏曲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和才能的重要途径
儒学宗教性内涵
一引言
儒家思想传统到底能否被视为一种“宗教”?这是二十世纪中外学术界关于儒学的重大争议性课题之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缺乏宗教内涵的思想传统,举例言之,民国8(1919)年2月,胡适(1891—1962)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此书的第四篇就以孔子为“实行的政治家”。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远流,1986),61。民国58(1969)年1月,徐复观(1902—1982)在他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二章讨论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第三章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春秋时代)之出现,并讨论宗教的人文化;第四章也是从宗教意识向道德意识的转化,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1969)这是五四以降中国人在崇拜“民主”与“科学”,追求理性的时代思想氛围之下,所建构的孔子与儒学的现代形象。这种孔子及儒学的形象,以其将“宗教”与“人文”峻别为二,终不免启人疑窦。
另一方面,儒学的宗教面向却也常常受到中外学者的注意,举例言之,远在1904—1905年韦伯(Maxweber,1864—1920)出版《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时,他是在“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脉络下,探讨儒学作为宗教之诸般问题(如缺乏“圣”与“凡”之紧张性……等)。MaxWeber,TheReligionofChina:Confucianismandtaoism(NewYork:TheFreePress,1951,1964)日本汉学前辈池田末利在1981年出版《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与思想》时,就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思想的宗教性格,讨论古代中国人崇拜之对象,祭礼之场所及礼仪等各方面问题。池田末利也讨论与儒学传统有深刻关系的春秋时性主义以及“天道”与“天命”等概念,认为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无神论的文化,认为儒家思想传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识,“天道”或“天命”的概念从早期的主宰的人格意义的天,转化为原理性的、哲学性的存在。池田末利,《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1),尤其是页956—957。池田末利分析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外显行为,未及其内部思想。当代新儒家学者在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书》时,更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但可惜并未深入论证儒家的“宗教性”这个问题。牟宗三、复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说:“我们希望世界人士研究中国文化,勿以中国人只知重视现实的人与人间行为之外表规范,以维护社会政治之秩序,而须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从事道德实践时对道之宗教性的信仰。”见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收入: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1974,199),引文见页145。牟宗三又说:“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台湾学生,1963),页99。1971年刘述先循田立克(PaulTillich)将“宗教”定义为“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之思路,认为儒学对现世精神之注重未必一定违反宗教超越性之祈向。孔子虽然不信传统西方式的上帝,并不表示孔子一定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怀。Shu_hsineLiu,“TheReligiousImportofConfucianPhilosophy:ItsTraditionalOutlookandContemporarySignificance,”PhilosophyEastandWest,Vol.21,No.2(April,1971),157~175;刘述先:《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对现代化的角度论儒学传统的宗教意涵》,刘述先主编:《当代儒学论集:传统与创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页1-32。1990年日本学者加地伸行也强调儒家重视生死问题,并特重葬礼,可以视为一种宗教。但是,加地伸行所强调的是儒家的丧礼之仪式,他并未深入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内涵。加地伸行,《儒教とはなにか》(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儒教”一词系自古以来中国习用之名词,《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晋书·傅玄传》:“政体存重儒教”,其涵义与“儒学”(《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德好儒学。”)并无不同。在一般日文著作中,“儒教”一词使用极为普遍,当系援用传统中国典籍中之用法,泛指儒家思想传统,但是,儒家的“宗教性”内涵,仍未获得充分论证。从德川时代(1600—1868)以降,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日本就习称儒家传统为“儒教”,当代日本学人亦以“儒教”为惯用语,例如:武内义雄,《儒教之精神》收入:《武内义雄全集》(东京:角川书店,1970),第4卷,儒教篇三,7—137;板野长八,《儒教成立史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95);荒木见悟,《佛教と儒教》(东京:研文出版,1993);冈田武彦,《儒教精神と现代》(东京,明德出版社,1994)。小岛毅最近对“儒教”与“儒者”之分际,曾有专文加以分疏,见:小岛毅,《儒教与儒学涵义异同重探》,《当代儒学主题计划》第二期小型研讨会论文,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年7月3日。
这篇论文写作的目的在于重新探讨“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我在这篇论文中想要论述的基本看法是:儒学有强烈的“宗教性”(religiosity),也有强烈的“宗教感”(senseofreligiosity),但不是西方传统定义下的“宗教”(religion)。因此,“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涉及所谓“宗教”的定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宗教”一词定义的再反省。必须在此特别说明的是:今日我们站在学术的立场重估儒家的宗教性内涵,与清末康有为(1858—1927)及谭嗣同(1865—1895)等人,在与孔教以求中国之富强的脉络中重估孔教之价值完全不同。参看,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成书于1897年,北京:中华,1988);谭嗣同,《仁学》,收入:《谭嗣同全集》(北京:新华,1954),页3—90。
为了比较清楚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本文第二节首先提出关于“宗教”一词的两种定义,厘清所谓“宗教性”一词的涵义,并说明儒学的宗教性见于儒者对世俗事务(如修、齐、
治、平)所抱持的绝对严肃的态度,这种虔诚之态度就是田立克所谓的“终极关怀”,由此展现一种“内在超越性”,本节接着再说明儒家的宗教性之文化史及思想史的渊源;第三节进一步分析儒家的宗教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展现方式,前者表现在儒者对古圣先贤的企慕与对传统的继承;后者表现在儒者个人与社会以及宇宙超越本体的互动关系。本文第四节则针对“儒学不是宗教”之两种论点加以检讨,进一步指出:在儒家的宗教感之中,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一种贯通面非断裂的关系。本文第五节综合全文论点,呼吁对于儒学的“极高明”的面向应加以重视,才能更深入地解读儒家经典的深刻涵义。
艺术学学科体系构想
[摘要]中国艺术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一,中国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与经典艺术作品,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各个艺术种类。除了通史以外,还有断代史等。第二,中国艺术门类众多。除了通常都有的绘画、雕塑、建筑、戏剧、音乐、舞蹈等门类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种类,例如书法等。与此同时,中国艺术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第三,中国艺术体系繁杂。在中国艺术史上,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还包括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方面和不同类别。第四,中国艺术成就辉煌,出现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和优秀艺术作品。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到艺术学的高度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关键词]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构建
人类的艺术史同人类的文化史一样古老。但是,艺术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学科,只是在19世纪末才在欧洲诞生,距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直到近几十年来,艺术学才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相对于文学研究和各个门类艺术的研究来说,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普通艺术学研究至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如何深入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宝藏,更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艺术学体系庞大,特别难以研究。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之外,还在于艺术学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大门类。在艺术学这个大门类中,包含着一般艺术学、音乐学、美术学、戏剧学、舞蹈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曲学等多个具体的艺术种类。其中每一个艺术种类都可以同文学相提并论。实际上,文学与艺术也是联系十分紧密的,甚至从广义上讲,文学也可以被称为人类的语言艺术。
在艺术学这个大门类中,又有作为具体学科的一般艺术学。一般来讲,作为具体学科体系的一般艺术学,应当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即我们常讲的“艺术史论”。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艺术学是涵盖所有具体艺术种类的普通艺术学,因此,作为学科体系的艺术学,它的艺术史应当是涵盖各个具体种类的艺术史,即中国艺术通史;它的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也应当是涵盖各个具体门类的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即我们平时所讲的艺术学概论。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作为学科体系的艺术学又涌现出了许多崭新的分支学科,诸如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教育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营销学、艺术传播学等等。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近年来都相继开设了上述专业或课程。此外,根据国别的划分和民族的划分,作为具体学科体系的艺术学又可以划分为不同国别的艺术学,正如文学可以分为中国文学、美国文学、俄国文学一样,艺术学同样可以划分为中国艺术学、美国艺术学、俄国艺术学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讨论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毫无疑问,中国艺术学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一,中国艺术历史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艺术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中国文学史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以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和样式一样,中国艺术通史也应当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与经典艺术作品,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各个艺术种类。除了中国艺术通史以外,由于中国艺术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都取得了独特而辉煌的成就,今后还应当采用断代史的方法加以研究,例如秦汉艺术史、唐代艺术史等等。第二,中国艺术门类众多。除了世界各国通常都有的绘画、雕塑、建筑、戏剧、音乐、舞蹈等门类之外,中国艺术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艺术种类,例如书法等。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例如中国的国画同西方的油画、中国的戏曲同西方的话剧都存在着十分鲜明的区别,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当然,作为中国特有艺术的戏曲,本身又包含着京剧、昆曲、越剧、豫剧等三百余个剧种,具有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等戏曲艺术审美特征,值得我们从艺术学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加以研究。第三,中国艺术体系繁杂。在中国艺术史上,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还包括文人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等不同方面和不同类别。就拿绘画和书法来讲吧,现在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历代的文人艺术家和宫廷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即文人书画和宫廷书画。实际上,在民间艺术和宗教艺术中,也有不少优秀的书画作品值得去发掘和研究。第四,中国艺术成就辉煌。中国艺术犹如一个巨大的宝库,历朝历代出现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宛若天上的繁星一样难以计数;产生了无数的优秀艺术作品,真可谓是浩若烟海,让人目不暇接。正因为如此,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庄暴见孟子语文教学教案
一、课文悟读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下》第一章,可以作为一篇对话体的议论文来学习。文章由叙人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全文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文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孟子的政治思想,故学习本文时,可让学生对孟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先作一些了解。
学习本文,还要对文中的一些文言语法现象,如词类活用、特殊句式以及常见词语、古今异义现象等加以摘录整理,做到能理解其含义、辨析其用法,以加强文言知识和语感的积累。为此,要求学生对文章反复朗读,力求做到熟读成诵,从而进一步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
二、亮点探究
1.齐王听到孟子谈到“好乐”一事,为什么会“变乎色”?
探究学习:学界出现了这样三种解释:齐王有不悦之色,认为孟子不该问自己“好乐”的事;齐王有羞愧之色,认为自己不应该“好乐”;齐王有愠怒之色,认为庄暴不该把他“好乐”的事告诉给孟子。权衡上述几说,以第三说为最佳。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竿,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禀食以数百人。”供养这样一支乐队,势必劳民伤财,并影响政事。孟子来齐国宣扬其“仁政”,劝说齐宣王“保民而王”,所以齐宣王心中要“怪恚”庄暴,不该把自己的隐情告诉给孟子。儒家历来重视礼乐,认为音乐具有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从音乐可以考察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并反对把音乐作为单纯的娱乐活动。“先王之乐”是先王用来教化百姓、安定民心、治理国家、巩固统治的手段,与“世俗之乐”截然不同。齐宣王爱好的不是“先王之乐”,而是“世俗之乐”,这又与儒家的音乐主张不甚吻合了。齐宣王之所以直言不讳地向孟子表白“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是考虑到隐情既已泄露,也就不必再转弯抹角了,免得孟子纠缠下去。而后来谈话之所以还能继续进行,是因为孟子并不反对他爱好“世俗之乐”。也有人认为:“齐王感到作为国君而爱好音乐,当为舆论所不许,怕受到孟子的批评,因而脸上表现得有点惭愧。”(李炳英《孟子文选》)其实,战国时期爱好“世俗之乐”的国君不乏其人,齐宣王也用不着为此而到“惭愧”。所以,齐王的“变乎色”应是“愠怒之色”。
明清江南市镇和农村关系史概说
[摘要]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透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