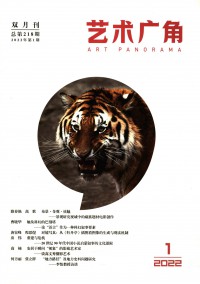艺术哲学论文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艺术哲学论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后现代哲学史讨论
一沃格林重新发现谢林
在二十世纪政治哲学经典著作《新政治科学》(1952)中,沃格林以灵知派世俗政治神学,分析当代集权主义尤其是原苏联的政治结构是如何可能的。沃格林独出心裁的见解是,原苏联的政制与其说是基于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基于俄罗斯—拜占庭的国家与教会一体的东正教政治神学,以及从异端灵知派经过约阿西姆(JoachimofFiore)的异端政治启示录流传下来的“第三罗马”的理论。而谢林的《诸世界时代》、《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中就到处充满着“第三世界时代”、“第三酒神”、“启示的宗教”,“圣灵的时代”、“第三基督教”、“约翰的教会”等先知式的历史预言。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事件》中同样特别地提及这一点。[1]谢林认为历史的力量在于灵魂和精神,哈贝马斯说他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先驱”是不对的。[2]谢林将政治和历史都视为灵魂和精神的政治和历史,这种唯心史观难道不是一种灵知派激进的末世论吗?谢林的历史哲学是否也该为整个现代性具有同一起源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种种灾难性后果负责呢?
沃格林认为,尽管谢林的“第三基督教”与约阿西姆的“第三时代”的政治启示录有紧密的关联,但是谢林的良好的平衡感使他没有陷入一种放纵不羁的“异端政治启示录的末世论”之中,正是这种没有约束的末世论才成为二十世纪东方和西方的集权主义的根源。按照沃格林的哲学,谢林试图以圣灵化的“第三基督教”克服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可以与柏拉图对过去的象征秩序的克服以及基督教对希腊神话世界的克服相比,这一新的象征结构直接以思辨的语言表达了新的灵魂的经验,整合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理性与信仰综合的意识结构。因此,沃格林说:“谢林的理念的哲学不仅一般在西方思想史上,而且也特别在政治思想史上建立了一个意识的新水平。我们可以试着通过比较谢林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与柏拉图在希腊历史中的地位标出这一新水平的特征。”[3]
沃格林认为,谢林的“级次学说”(Potenzslehre)在基督教的思想内,直接地表达了灵魂的意识对整全和历史的意义。而没有经过基督教的柏拉图则以神话的方式表达了这一意识水平。沃格林给予谢林的哲学的平衡感以极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将谢林的地位与阿奎那的地位做以比较。如果说阿奎那的体系是试图在欧洲高等文明破裂分散入各种此世的特殊的共同体之前,协调其张力的一种努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谢林的体系是在欧洲最后的文明破裂分散入我们时代的危机之前,平衡其全部张力的最后的巨人般的努力。”[4]
沃格林将谢林视为二十世纪的危机前的十九世纪的综合、平衡、和谐和集大成。沃格林认为,谢林是自1300年中世纪大一统的分裂之后再次将笛卡尔以来的变乱的和对立的各种哲学语言和基督教的语言综合起来的哲学家。谢林本人也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称谢林是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以往哲学流派的“吹牛大王”。[5]沃格林认为,谢林不仅通过回归布鲁诺和波墨,克服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对自然的遗忘,而且还通过新泛神论体系克服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泛神论与单子论的表面对立;他不仅通过自由体系克服了康德的先验的、形式自由和费希特的主体性的自由的困境,而且还通过其晚期的存在主义克服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体系;他不仅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对神话的哲学思考克服了理性主义设定的界限,而且还通过级次说克服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他不仅以其基督和酒神的新神话学直接开启了荷尔德林和尼采的酒神颂和酒神哲学,而且还以其艺术哲学开启了二十世纪“艺术至上”的趋势……
沃格林说:“在谢林之后到来的是他以灵魂的力量将它们聚拢在一起的那些要素的剧烈的分裂。结果我们在他的下几代看到了他的经验的各个部分的溃散:在叔本华那里的意志的经验和涅槃的经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的回归内在的渴望;在弗洛伊德那里的无意识心理学;在尼采那里的酒神体验和此岸的恩典的经验;在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大众运动中的对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对第三王国的渴望;在尼采、弗洛伊德那里的在世界大战的毁灭和自我毁灭的高潮亢奋中伴随着焦虑的对恶兆的狂欢的经验。这些要素的分裂标志着时代的危机,而这些要素的平衡则标志着谢林的伟大。谢林从不期待着它们的溃散,而且他也很少引起它们的溃散,因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文明地震的地震仪,而不是它的起因。(略)因此,谢林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而不是一个开端;他作为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就如同柏拉图、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那样。但是,在他的著作标志着文明时代的终结之时,他也建立了意识和批判的新水平。对于那些被围困于一片混乱的示微的传统、各种相互冲突的末世论、现象的思辨和迷狂、各种意识形态和纲领、盲目的仇恨、各种狂欢的毁灭等等之中希望获得一个坚实的立脚点人来说,谢林的成就作为定位点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中具有与日俱增的重要性。”[6]沃格林从他自己对实在的整全经验的思想、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视角和当代的时代危机的问题背景解释了谢林思想探索的意义和地位。我们即使不能断定沃格林的评价恰当与否,至少这种评价可以改变我们所接受的庸俗哲学史教程中的谢林形象。
音乐美学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音乐美学;舒曼;感情论
【论文摘要】:罗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机会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音乐,更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音乐的贡献。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舒曼则主张"感情论"具有特定的美学内容,带有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著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舒曼音乐教育艺术
【论文关键词】:音乐美学;舒曼;感情论
【论文摘要】:罗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机会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音乐,更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音乐的贡献。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舒曼则主张"感情论"具有特定的美学内容,带有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著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艺术哲学现代转型中
一、艺术文化的转型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突变的时代。引起这场突变的因素有来自西方的冲激,也有来自传统自身的裂变。这种变化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种变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们的心灵深处。中国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近代艺术萌发的新旧交替和转型就是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过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见全集第二卷)中国当代有的美学家还不厌其烦、一论再论“美是和谐”的观点,可见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追求,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肯。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要求把构成艺术的多种元素如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古代艺术的实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想来规范和陶铸的。
中国古典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现世俗和人情为核心的广阔世界。小说和戏曲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的代表。明代资产阶级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下层的市民文艺和上层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开,袁中朗、汤显祖、冯梦龙、吴承恩、李贽等风靡一时并连成一气。不料满族入主中原,强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盘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李泽厚《美的历程·十》)于是浪漫变成了伤感,对朴实而充满朝气的市井生活的描绘变成了对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到晚清,伤感愈深甚至悲鸣,激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爱国歌》(康有为的一篇长诗),所见是《革命军》(邹容),所闻是《盛世危言》(郑观应)、是《警世钟》(陈天华)……古典主义的和谐完全被历史的巨轮所辗碎。石门锁不住,黄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艰难地升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术革命、还有文界革命、戏剧改良,一时间舞者如潮。
如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近代艺术演变也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体的渐进过程。比如,诗界革命就未能突破旧风格,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小说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的矛盾,而美术革命也意识到要改良中国画,不能只限于模仿一点西洋画的技法,而必须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还有古文的衰微与新文体的诞生更是如此。如梁启超则以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无所顾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体,即所谓“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归纳说明:“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里除提及“外国语法”一点之外,其余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特别是他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且两方面都极度扩展,并行不悖,更是发扬了情理并重、一体圆融的古典艺术精神。因此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可以说近代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在发展。
中国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理性早熟的农业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为审美理想的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有进步则有过渡”,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这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艺术文化模式在酝酿,形成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无根的,它应该是传统的新发展。其次,它又面临着西方艺术文化的挑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作出回应,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种审美价值观,并树立一种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传承、审美心理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凝结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
哥白尼转折
1994年,布兰顿发表了正文厚达741页的代表作《清晰阐释》(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贝马斯发表长篇评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1],高度评价了布兰顿的贡献,称这部著作为“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如今,布兰顿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2]在人才济济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这位美髯公与麦克道尔(JohnMcDowell)一道堪称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样于1994年出版的《心灵与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誉为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